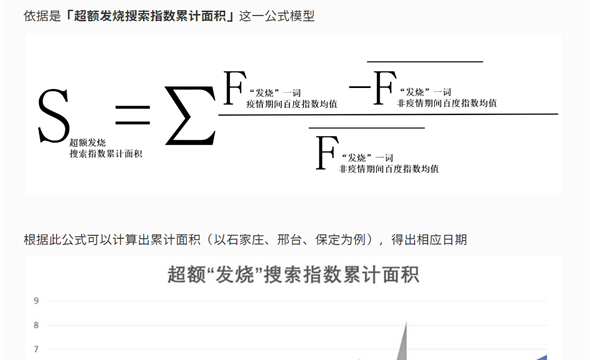中美货币政策调控往往相异。除了经济周期不同步造成中美货币政策方向往往不一致外,在货币政策工具运用上,中美两大经济体也各具特点。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运用以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主,并且越来越多使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美联储虽然也会使用数量型工具(如量化宽松、资产购买等),但总体上仍以调节联邦基金利率为主。
一、我国货币政策运用以调整法准为主,美国则以调节利率为主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法律规定的商业银行准备金与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比率。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不能全部放贷出去,必须按照法定比率留存一部分在中央银行。目前我国根据银行规模大小划分了三档存款准备金率,工农中建交和邮政储蓄银行六大商业银行实行10.75%的存款准备金率,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和部分规模较大的农村商业银行实行7.75%的存款准备金率,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社、村镇银行、服务县域的农村商业银行实行5%的存款准备金率。
2016年以来,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过20次,均为向下调整(降准)。其中,有8次下调了0.5个百分点,4次下调了1个百分点。而同期我国政策利率(如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调整过12次(最近两次下调政策利率分别是在今年6月和8月),其中,向上调整(加息)4次,向下调整(降息)8次,每次以调整5到10个基点为主,最多的一次性下调幅度为15个基点。目前1年期MLF利率为2.50%。
相比之下,美国货币政策运用以调节利率为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联储主要采用调节短期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来达到就业和通胀的双重任务目标。所谓联邦基金利率,就是商业银行借入或融出准备金的利率。至今,这一利率仍是美联储主要政策工具。2016年以来(截至2023年8月31日),美国政策利率(联邦基金利率)调整过24次,向上调整(加息)19次,向下调整(降息)5次,每次以调整25个基点为主,疫情以来,调整幅度较大,以50个基点为主,甚至高达75个基点。目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5.25%至5.5%。
在决策程序上,美联储进行利率调控的便利性远高于准备金率的调整。美联储调整利率主要通过每年在华盛顿召开的8次议息会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的成员投票决定联邦基金利率升降。美国调节法定准备金率则更为复杂,需要对美联储法案Regulation D(Reserve Requirement of Depository Institutions)进行修改,该法案修改需由联邦储备委员会(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批准同意。联邦储备委员会是美联储的管理机构,监督储备银行的运作并提供一般性指导。7位委员均由总统提名、国会任命,均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虽然美联储调节法定准备金率并不需要国会的直接同意,但仍要经过内部一系列的分析讨论后,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批。由于法定准备金率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利润,美国自由主义传统、选举压力以及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都使得美联储在使用这一工具时比较慎重。
自20世纪90年代,美联储几乎不再使用存款准备金工具。与中国的“三档”准备金率不同,美联储是对不同账户(净交易账户、非个人定期存款、欧洲美元存款)、不同金额(针对净交易账户)设置不同的准备金率,机构之间的规定是同样的。1990年12月27日,美联储将非个人定期存款、欧洲美元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设为0,且一直保持不变。2020年3月26日,美联储将净交易账户的法定准备金率设为0,此前则规定:净交易账户中低于“准备金要求豁免金额”的,其准备金要求率为0;超过“准备金要求豁免金额”但低于“低准备金部分”这一指定金额的,其准备金要求率为3%;超过“低准备金部分”的,其准备金要求率为10%。至此,美国所有金融机构的所有存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0。
二、我国货币政策实施更需要商业银行体系的配合
与财政政策可以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不同,货币政策一般是间接发挥作用的,需要商业银行,甚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配合,其实施效果在相当程度上受市场反馈的影响。
一般而言,紧缩的货币政策更容易对经济产生影响,而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需要通过流动性宽松鼓励信贷扩张时,商业银行往往“惜贷”,央行宽松性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的过程就会受阻,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则大量增加。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商业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大幅提升。直到现在,美国商业银行的超准率仍高达15.3%(2023年7月)。这样的情形下,准备金率政策的实施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以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例,由于商业银行超储率很高,一部分超额存款准备金转化为法定存款准备金,银行的流动性约束几乎没有变化。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仅有1.6%(2023年6月),较3月末下降0.1个百分点,并且为2022年以来最低值。此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流动性改善是比较有效的。
我国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因而商业银行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作用就更为关键。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途径少、资本压力较高。在此背景下,将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与利润维持在一定水平,能够有效帮助银行补充核心资本,增强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从LPR报价看,1年期LPR为3.45%,5年及以上LPR为4.2%,均已处于2019年8月LPR改革以来的最低值。这体现了目前我国逆周期调控政策中,金融部门向企业部门让利。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3万亿元,同比增长2.6%,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4.5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处于历史低位。截至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74%,为2010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相比之下,海外银行在近期连续加息的背景下,净息差已经大幅恢复,美国银行的平均净息差已经达到3.3%以上。净息差高于不良贷款率将是防范银行风险的重要保证。
三、我国消费和投资的利率弹性较低,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期
从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经验来看,经济高增长时期和平稳增长时期的利率弹性比较高;在经济增速不佳的时候,利率弹性往往是很低的。这是因为,在经济上行期,居民收入提升,往往更愿意消费和追逐投资收益,此时利率调整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明显;在经济下行期,居民收入增速转弱,其倾向于增加储蓄、延迟消费,此时降息对促进消费的作用可能更为有限。类似地,经济上行期企业投资回报比较高,其融资需求对利率变动比较敏感;在经济下行期间,企业投资主要考虑的是风险,而不太会考虑利率成本。所以,在经济下行期,投资的利率弹性也不高,即使调低利率,也未必能拉动投资。
今年以来,利率下行与消费降速并存,这意味着单单依靠降低存款利率可能难以带来居民消费的提升。原因有很多。首先,在预期未来收入下降时,居民会审慎考虑当下的消费选择。其次,资产价格低迷将强化居民降杠杆意愿,进一步抑制消费。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较为低迷,以中长期按揭贷款购房的居民,其资产端预期收益下降并可能低于负债端成本,因而更倾向于提前还款,而不是增加消费。最后,居民风险偏好逐渐降低,预防性储蓄持续累积,也会拖累当前消费。2018年至2021年,我国居民部门每年平均新增存款为9.5万亿元,2022年则高达17.84万亿元,而2023年一季度新增存款就为9.9万亿元,1-7月累计新增11.1万亿元。
此外,我国利率市场化未最终完成,部分重要利率仍未完全市场化,例如存款利率。这意味着,我国政策利率变动对其他市场利率的影响还不强,从而对投资和消费的调控效果还有待提高。这也是我国央行较少调节政策利率的原因之一。否则,在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过度依赖利率调控不仅不能达到政策目的,还有可能带来潜在金融风险,如流动性淤积在金融体系等。相比之下,美国居民和企业的投资和融资渠道较丰富,利率市场化程度高。美联储调节政策利率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利率随之变动,从而对居民和企业的消费、投资产生较为直接和明显的影响。
四、中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的方式不同
目前我国国债中69%左右由商业银行持有,地方政府债中86%左右由商业银行持有。今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截至8月末,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已发行全年额度的82.5%,而去年同期为96.4%。财政部表示,今年新增专项债券力争在9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而降准将增加商业银行可自由使用的资金,从而更好地支持国债和地方债发行。从这一点看,我国降准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而美国国债持有者更加多元化。截至2022年末,美国国债的29.7%由海外投资者持有,在国内持者中,美联储、商业银行、政府基金和其他机构分别持有美国国债的20.7%、7.3%、6.1%和36.2%。与商业银行相比,美联储是美国国债更重要的持有者。尽管美联储已经启动了持续性的缩表,但目前其持有美国国债仍超过5万亿美元,占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的61.6%。
美联储成为美国国债的重要持有者,与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期间,美联储大量增持美国国债不无关系。当时美联储通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同时推动美债收益率下降,可使新发美债票面利率降低,减轻美债利息负担。这是从宏观政策协调配合的视角下,中美货币政策调控的又一个不同。
五、中美货币政策对外溢效应考虑不同
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货币,美元流动性遍布全球,美联储货币政策外溢效应也很明显。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任总统时期的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就曾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一语道出了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本国和海外影响的不对称性。本轮美联储加息的激进程度是罕见的,同样产生了很强的外溢效应。欧元对美元一度大幅贬值,甚至于2022年7月跌破了欧元兑美元的平价,为2002年以来首次。
我国货币政策在“以我为主”的同时,也需要兼顾内外平衡。目前处于经济恢复的关键期,还应该继续加强逆周期调控,这有助于夯实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但加力逆周期调控可能持续加剧中美货币政策的分化。从海外看,前不久在杰克逊霍尔刚刚召开了全球央行峰会。这次峰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都表达了对于通胀的担忧远超对于经济下行的顾虑,传递了超过市场预期的“鹰派”信号。
我国利率调整的信号效应比较显著,货币政策更倚重准备金率的调节。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7.6%,仍有一定的政策空间。
总而言之,造成中美货币政策调控差异的原因有很多。除了货币政策决策机制不同,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商业银行体系在货币政策实施中起到关键作用,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效率也相对更高。目前我国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较低,货币政策目标多元化,以及兼顾内外平衡的需要,也造成中美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差异。
本文来源: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陆家嘴金融网
作者:盛松成